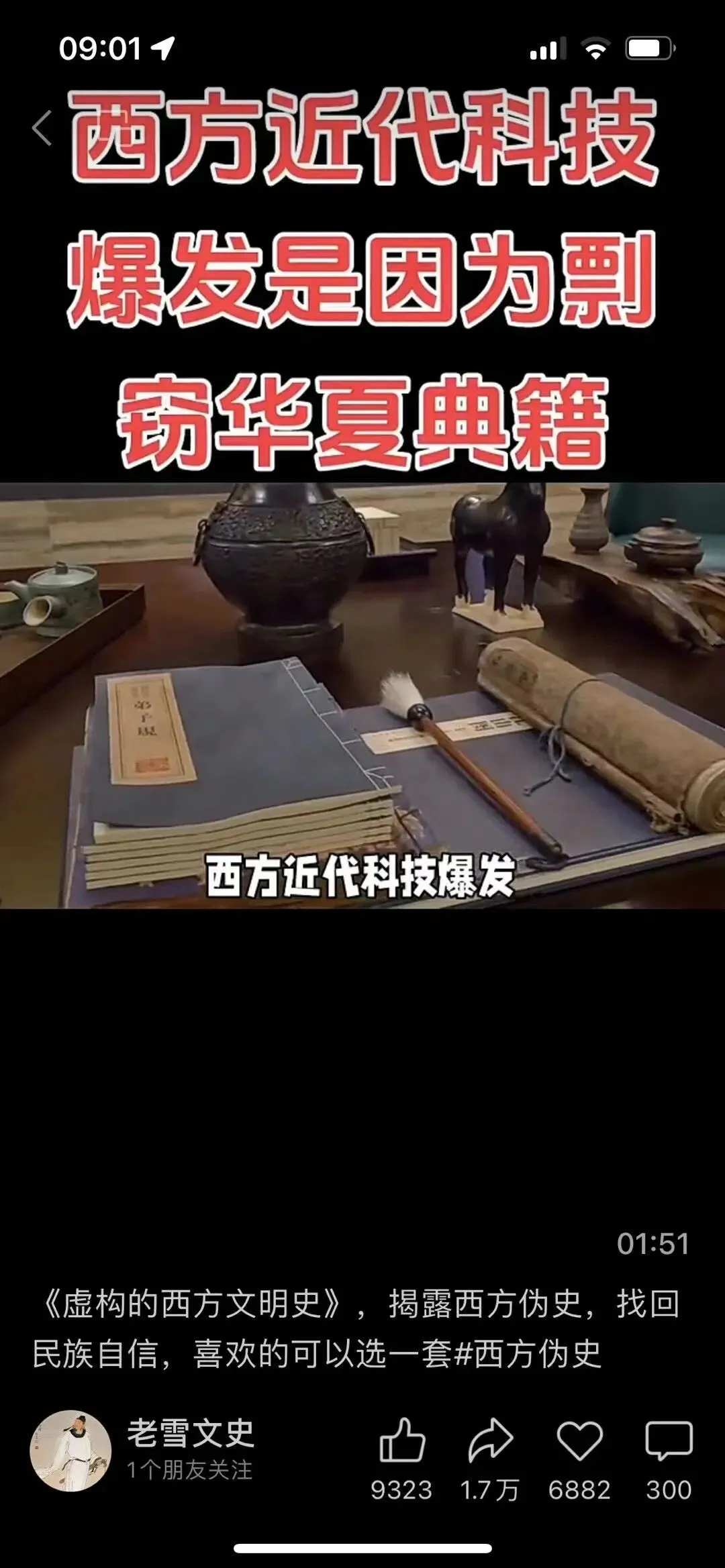钱锺书在《围城》中写过一个精妙桥段还记忆犹新。汪处厚向来客方鸿渐、赵辛楣炫耀他南京的房子,又故着达观地长叹:“这算得什么呢!我有点东西,这一次全丢了。” 他口中的“南京的房子”——那所“幸亏没被日本人烧掉”的豪宅——成为战乱时代最体面的精神铠甲。钱锺书用电影旁白式的语气调侃到:“日本人烧了许多空中楼阁的房子,占领了许多乌托邦的产业,破坏了许多单相思的姻缘。”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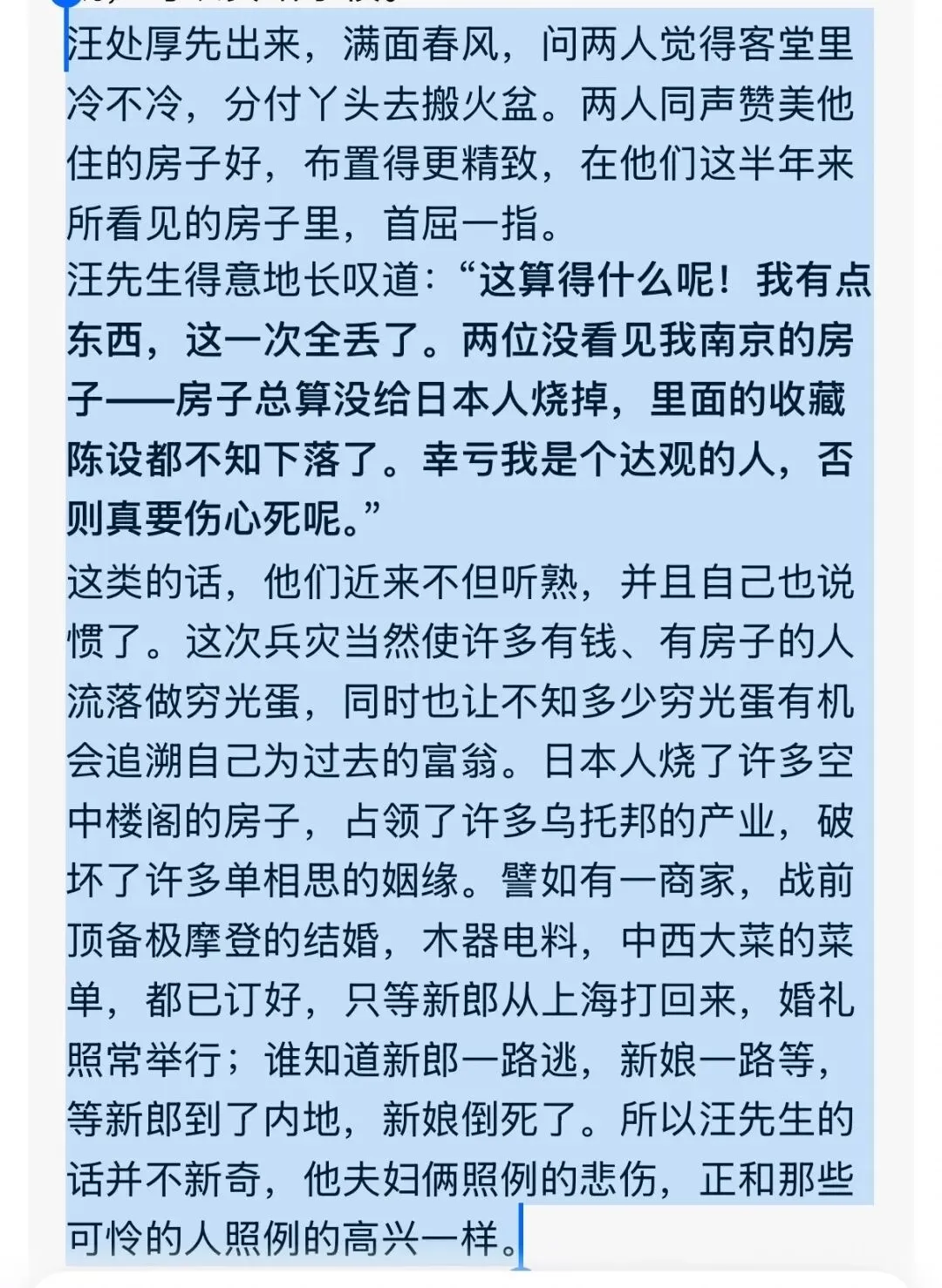
八十年后的今天,这幅图景在“西方伪史论”中复活了。《永乐大典》正成为网络“显学”:它不再是一部散佚严重的明代类书,而被重构为“包含西方全部科技源头”的万能宝库——蒸汽机、微积分、解剖学,皆可从中找到雏形,只是“被传教士偷走了”,才导致中国落后。这就是汪处厚逻辑的当代版:将真实的文化创伤(典籍散佚、近代屈辱)转化为无法证伪的辉煌故事。现实的无力感难以消除,便虚构一个“曾经拥有一切”的过去。穷光蛋追溯为过去的富翁,边缘者幻想为被窃的霸主。

更深层的悖论在于,这种“反西方”逻辑,恰恰以最卑微的方式承认了西方的标准。伪史论者激烈争夺“谁先拥有科学”的优先权,却未质疑科学为何仍是衡量文明的唯一尺度。他们拆毁了西洋招牌,却将自家牌匾挂在同一根柱子上。方鸿渐的克莱登大学文凭提供了另一重镜像:他明知文凭是假的,却仍需要这个“西洋符号”获得社会认可。伪史论者一面痛斥西方中心主义,一面用“我们比西方更早”的句式,完成了一次焦虑式的文化献媚。
《永乐大典》的真实命运本就足够沉重。三万七千万字的嘉靖副本,历经明清鼎革、八国联军、清末监守自盗,今存仅四百余册。这是文献学的悲剧,值得严肃追问。但当悲剧被改编为“因西方盗窃才引发大航海和工业革命”的爽文,历史的复杂性便消溶于廉价的民族激情。

钱锺书笔下的“单相思”道破了此中玄机。伪史论者与《永乐大典》的关系,恰如汪处厚与南京豪宅——并非真实的占有,而是单向度的想象投射。真正的文化自信,应当敢于直面历史的全部复杂性:承认《永乐大典》的编纂伟业,也承认其文献局限;哀悼典籍散佚的命运,但不将其神化为失落的亚特兰蒂斯;正视近代化挫折,却不将其简化为一场有预谋的盗窃。
否则,我们便与汪处厚坐在同一张红木椅上,在砖地火盆之间,交换着那些“听熟了、自己也说惯了”的辉煌往事——用一座永远无法抵达的“南京豪宅”,抵御近代百多年来真实的心理落差。
您认为,我们今天追忆老祖宗的辉煌“曾经富过”是安慰自己,还是提醒未来?欢迎留言讨论。